
所以,很美的风景,我却将它们拍得烂。最好不要怪我,要怪就怪那只骗人的镜头好啦 
D5 1月24日 农历腊月二十九
凌晨3点45分,被起床铃声铁面无私、冷若冰霜地叫醒。4点15分,睡眼迷离地登上了旅游公司的车子,可怜的导游也陪着大家一起早起,酒店门口目送车子的离开。
天黑黑。车里亮着灯光,车窗外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只能用它来看看车里播放的中文DVD录相,内容当然与接下来的活动有关。注意事项播放完毕,缩在座位上,入梦。
一个小时的车程,目的地到了。睁开清亮的眼,黎明前的黑暗已经过去,虽然还有些许的暗淡,但毕竟天已经亮了。
齐腰深的草地里,九个庞大的热气球(hot air balloon)整整齐齐地排成一排,不时呼呼地喷几口炙热的火焰,将气球吹得鼓鼓胀胀的,以圆润的身姿,做着起飞的准备。蓝的黄的红的热气球,图案 简单明了卡通味儿十足,蓝底的配上金色的世界地图,黄底的绘上土黄的袋鼠,红底的画上灰白的考拉,可爱至极,内心深处被深深感动,发出无言的惊呼,心扉被撞击得神旌摇动。



几分钟内,天空也被火焰点燃了,熊熊燃烧起来,有谁见过清晨的火烧云吗?如此浓情,如此大胆,如此热烈,让我的心中,打翻了五味瓶般说不出滋味。在佛教徒眼里,最虔诚的是佛光;在基督教徒眼里,最坚强的是主耶稣;在天主教徒的眼里,最圣洁的是圣母玛丽亚。而在我的眼里,涌动的是无缘无故无所事从的泪,终是不够坚强,不小心被大自然的壮美撞到,深深折服,深深动容。

镜头里的草尖被镀上了一层朦胧的金色,树木披上了金色的外衣,卡车开进来,扰了清晨清静的梦。同团的队友共10人选择乘坐热气球,为此特意换了长裤波鞋,以防来自蚊虫的叮咬及高空的寒冷。
蹬上黄色袋鼠图案的气球,藤制的筐子边缘密实地包着海绵,上上下下时抓在手里很是舒服。筐子分左右两边,每边分前后两排,每排供五人容身,美中不足的是只有站位没有座位。筐子内侧安有粗壮的绳索圈,下降时要求双手紧握,做下蹲打马桩状。筐子的正中间,是氢气瓶的地盘,还有瘦高英俊热情洋溢的驾驶员。扛着摄像机的工作人员走过来,以家庭为单位留下合影,当然,买不买单,还是自愿。

氢气瓶比煤气罐高一些,后勤工作人员换了新的气瓶,一切起飞的准备均已就绪。慢慢地脱离地面,气球稳稳缓缓地升上天空。那层绚丽的红云已经褪去,变作清清淡淡的灰。太阳已经升起来了,害羞地躲在云层后面,星星点点裸露的天空,透着轻轻纯静的蓝。也许是相机档次有待提高,也许是摄影水平还滥竽充数,被景色的壮丽、秀美撞得心都痛了,却不能真实地记录下来。

在1000-1500米的美丽宽阔的亚瑟顿平原上空鸟瞰脚下的农场, 整齐的农田,成片的芒果树,间隔的蓄水池,一派悠闲浓郁的田园风光。不远处的空中,上上下下的飘浮着其他几只气球,相互做映 衬,彼此成背景,五颜六色的装点着天空。在驾驶员的指挥下,目光齐刷刷地望向前方悬挂着的相机,亮出清晨的清纯笑脸,这次轮到摇控器伸出援手,拍下空中的集体合影。




当风景逐渐看够,大人孩子的口中还念念有词,期待着袋鼠的出现。果然不负众望,路过一片野生小树林时,五只排成一队的袋鼠蹦蹦跳跳的身姿,忽的跃于林间的空地之上,令群情激昂,激动万分,振臂高呼。袋鼠的名字来自土著语,意思是“不知道”,而我不知道土著人当时到底想知道什么。

Landing对于热气球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,由于风速的原因,降落的地点很随机。驾驶员的技术不错,半个小时的飞行接近尾声,气球稳稳地下降,找到田间一条狭窄的空地,降落在齐腰深的野草丛里。拖着瘦长拖车的轻型小卡车马上赶来,带来了下一批的乘客。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,有条不紊地下来两人,再上来两人,以保持气球的重量平衡。

坐在卡车的铁车帮上,在田间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簸,一向养尊处优的屁股实在受不了这份罪,蹲下来更好受一些。回到平整的路面,回程的巴士却没有来程时那般及时,终于等来了一辆大巴,却另外还有接客任务,目标锁定在那只因为找不到落脚点,还在天上闲逛的黄色气球上的乘客。
车子追着气球跑了一段路,司机判断说气球要降落了,愿意帮忙收气球者,请上后面跟着那辆卡车。一向好奇心重的我,率领胖子和小宽一马当先,跳下大巴跳上卡车。又是田间土路上无情的颠簸,转着圈,气球却高傲地不肯落下来。
回到大巴上继续追着气球远去的方向行驶,路两边是茂密青翠的甘蔗田,和家乡的稻田同一景致。澳大利亚人种植甘蔗的同时,在上风处按6:1的比例同时种植大豆。风起时,大豆散发出的氮气刚好被吹到甘蔗田里,不费吹灰之力就为甘蔗施了天然的氮肥,坐享其成就是这么简单。既然种植大豆的意义在此,那么不追求多高的产量,田里的大豆像澳大利亚的人口一样稀稀落落的。为农作物灌溉的水管裸露在地面上。软软的,均匀地分布着可开可关的放水孔。
在两片甘蔗田间的空隙处,那只顽皮的气球终于决定着陆了。三个人再次情绪高昂地跳上卡车,沿着排水沟边的土路开进去,气球刚好降落在排水沟处。气球里的人,正乖乖地等着我们的到达,只有大方无私地出手相救,他们才能顺利地走出气球。男人们兴师动众、兴风作浪、兴味盎然、兴高采烈地冲上去,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,一个人在正前方拉着绳索掌控方向,另外的人则七手八脚、齐心协力地把瘪得不成形状的气球彻底按倒。胖子的情绪很是高涨,很是high,手脚并用,嘴里还发出大声的叫喊。小宽也一直在帮忙,负责牵绳,可惜被气球挡住了视线,看不到他的忙碌。

而手无缚鸡之力的我,虽然没有参与到收气球的行动之中,却一刻也没闲着,躲在不会被气球砸到的方位,忙前忙后,忙左忙右地拍 那些漂亮的沾着露珠的草。身后是茂盛的甘蔗,天上是淡淡的鱼鳞状的云,如何能够错过这难能遇到、美不胜收的乡间景色呢!




待胖子忙完了,不放心地走过来,我的裤腿上已经沾了一层泥巴,鞋子也被露水打得湿透了。张张嘴巴,不知何时钻进牙齿间的沙尘吱吱作响。再看看手中的相机,也没能幸免地蒙了一层土黄色的尘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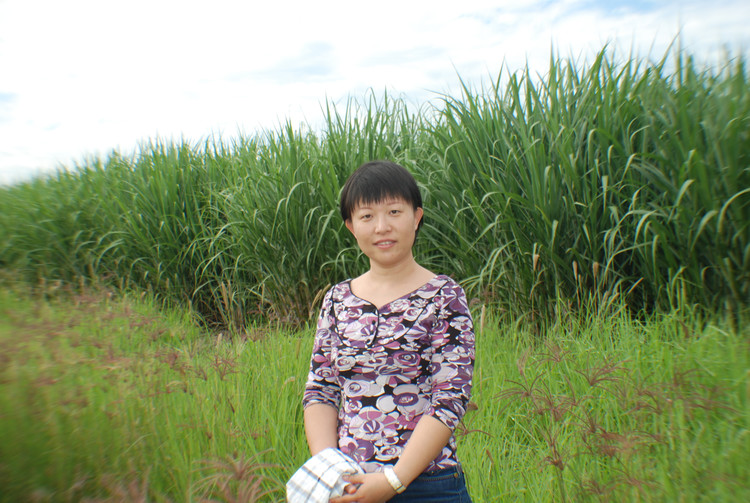

重新回到大巴,被带到可以进食早餐的乡村农场,卖点是香槟,美其名曰“香槟早餐”。时间已经是上午9点30分,尽管这一大早上,经过了几番折腾,经历了太多惊喜,肚子却并不感觉饥饿,这就是精神食粮的作用吧!早餐的品种少之又少,除了面包,咖啡,牛奶,稍有食欲的就只有咖哩炒饭了,淋上一点西红柿汤汁,再来半块熟西红柿,囫囵吞枣地下咽。今天的西红柿上,星星点点地洒了干茶叶碎末一样的东西,尝不出什么特别的味道,不知为何物。乡村早餐的水果却是丰盛的,芒果肉被切成小块小块的;火龙果的果肉只有鸡蛋般大小,粉得紫黑紫黑的,味道也更甜一些,也许是野生的吧;柚子皮是淡红色的,个头比橙子稍大些;还吃到了新鲜的奇异果。
工作人员拿来一支香槟酒,成人都可以品尝,酒精的味道很浓,冰冰凉凉的,不知是煽火还是降火。坐在实木做成的又宽又厚的桌椅边,一边聊着天,一边吃着喝着。餐厅没有门窗,只有不漏雨的棚,小鸟不时飞进来,捡点食物残渣当零食。一只螳螂误以为门柱是树木,也扛着长枪闯进来,觉醒后的撤退却颇费周折。出于对生命的尊重,不能出手相援,看着它小心奕奕、一点一点的挪动,移开。


吃过早餐好一会儿了,左等右等接人的车子也不来。在餐厅附近无聊地转着圈,前面是一片以桉树为主的树林,原始而稀疏,似乎无人修整,因为枯死的树就横在脚边。树林里开着淡紫色的野花,有的形单影只、孤芳自赏,有的拉帮结伙、成片成群,与夏天时在内蒙古阿尔山公园门前见到的如出一辙。树林里,小路边,随处可见蚂蚁窝,大的直径、高度一米有多,小的细细尖尖的,像被缩小了的塔。不远处围起了铁丝网,网的那面是一处地势起伏的牧场。牧场上青草茂盛, 也有树林穿插其中,成群的牛、羊、马在悠闲地吃着青草。天空中是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白,初起时云厚,渐渐的变薄,释放出更多明亮的天空。


同行的团友中,一个对紫衣情有独钟的王姓女人,看面相就知其蠢,经过几天的同吃同行,更甚。同样是等待,别人只是抱怨几句旅游公司的不周,就到清新的大自然里自娱自乐去了。蠢女人却登上了一辆其他团队乘坐的小巴,用沉沉的屁股占位,不肯下来,还按住车喇叭,发出阵阵撕裂般的车鸣。一矮个子的服务员怒气冲冲地走过来,脸色气得发青,也许是胡子重又刮得太干净,但他的愤怒却是显而易见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的,说这种行动是 “rudely,very rudely,too rudely”。作为中国人,我也愤怒,也被同胞的无知无礼,丧尽了颜面。
同伴的无礼,是真的惹怒了老外,接下来本该由他进行的调度,顺理成章、理所当然的变成了消极怠工。大肚能容天下事的胖子上前好言好语询问,第一次,那个光头服务员象征性地拨了电话,说车子已经在驶来的路上了,只需再等ten minute。过了10分钟还不见动静,胖子再上前去问,他却说他也管不到,车子的问题不属他职责范围内的工作,但他可以提供巴士司机的电话,我们可以自己去与司机联系。见胖子一脸焦灼与无奈,他装腔作势地说大可不必如此紧张,为什么不relax下来,何况还有coffee可以解闷,只要大家都safe 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,没有什么好着急的!我们着急,是因为行前约好了11点30分要退房,而此时已经是10点过半了。
此路不通,再开一路,机警睿智的胖子发现餐厅后面的一间模拟树屋里还有一个女员工,就谦卑地走过去,请她帮忙询问what trouble happened。胖女人满脸微笑,热情地伸出援手,又是打电话又是用对讲机,然后满脸堆笑地告诉我们车子马上就会来。果然如她所述,很快就坐上了车子。

同时坐上来的,还有其他几个团队的中国游客,彼此的遭遇堪称如出一辙,颇有同舟共济的互怜意味。当发动机发出可爱的轰鸣,高悬已久的心终于可以暂时放下来,困意同时袭来,闭上眼睛昏昏睡去。
再睁开眼睛时,发现车子停了,而我们并没有回到酒店,而是正置身于前天来过的库兰达热带雨林景区门口,原来旅游公司是先送几名来自上海的游客到此一游。
又被澳大利亚人给耍了耍,这个哑巴亏吃得更加无可奈何。上海游客的运气当然也不比我们更好,他们人虽然是在车子上,行李却不知置身何处,眼前能抓住的,只有车子和司机,在找不到行李的确切下落之前,哪肯放弃这救命的稻草移步下车呢!一头卷发漂漂亮亮的上海女孩,英语不错,只是有些口吃,站在车门口与司机交涉。作为同胞,同情是必须的,而足足一刻钟过去了,上海女孩还赖着不肯下车,耽搁的是大家的时间。不约而同齐声抗yi,上海小姐的脸皮还真是厚如城墙,直到得知装行李的车子已经驶来的消息,才放了我们一条生路。
被上海女孩放行,又被一台湾女孩劫持。她要去的地方是缆车站。路过一换乘站时,车上只留下台湾女孩,其他人均被转换到另外一辆中巴上,没有全体护送台湾女孩再到缆车站,不知是大家的不幸还是幸运。午后近一点钟,历尽千辛万苦,经过万千磨难,终于百转千回辗转回到了酒店。远远地看见导游小刘,正一脸无辜地坐在酒店门口的平台上,翘首企盼大家的平安归来。没去乘坐热气球的另外九个人,都坐在大堂里整装待发,而之所以还没出发,欠缺的正是这股恼人的东风。
冲进房间,以军事演习的速度换下脏衣服,收拾好行李,寄存在酒店大堂。刘导带领大家步行到不远处的“饮食天”餐厅吃午饭,当然还是中餐。入座时导游面授机宜,要求乘坐热气球的十人一桌,其他九人坐另一桌,原因是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会赶来向大家say sorry。
刚刚坐定,旅游公司派出的代表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了,言语间承认因为工作失误而给大家带来了困扰,真诚地向大家道歉,并保证以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他们解释工作出错的原因,是因为今天游客爆增,忍不住掐着指头为他们算了算,其实每只气球可乘坐20人,10只气球也不过200人,就算每只气球可以接待两波客人,也不过400人的客流量。怪只怪澳大利亚人口稀少,换做在中国,谁好意思拿400人说事啊,4000人、40000人又算得了什么呢!为表诚意,旅游公司为我们这一桌加了一支当地产的比较有名的红酒(说得太快,没记住名字),还有一道炒螃蟹,另外一桌则没有这样的待遇,这就是老外的行事风格,见怪不怪。红酒每人尝了一点儿,那两只被炒的螃蟹活着时长着一副又黑又宽的身材,炒熟了端上来的,却只是空空的壳,蟹肉严重缩水,淡淡的没有滋味。
午餐提供的其他几道菜肴,和昨天的晚餐如出一辙,还是卤得软软的鸡腿鸡翅,蒸制的白白嫩嫩的鱼片,芹菜胡萝卜炒牛肉,韭菜炒鸡蛋,水煮生菜,还有靓汤。
旅游公司的道歉是节外生枝、意外收获,知道自己是个非常容易满足的人,找到了部队,没有误了即将飞往悉尼的飞机,之前的焦虑算不了什么,人生中哪有不吃亏的时候,怎能不遇坎坷啊。仗义的东北男人胖子,则难平心中的积怨,挺身而出主持公道,质问导游,为什么收到了老外的道歉,却没有一句来自他的道歉。因为出了问题之后,大家谁都没有接到来自导游的一声问候或一个电话,在大家最彷徨无助最需要他出面安抚的时候,他却不知躲到了哪里。导游讪讪地所问非所答,用他习以为常的讲话方式,绕着圈子讲着罗圈话,迟迟不肯切入正题。也不难为他,彼此心知肚明,接下来的行程是否尽心尽力,全凭他的悟性了。
饭后已近两点,眯着眼睛,穿过烈日炎炎下明晃晃的街道,步行回到酒店大堂。距离赶往机场的时间还有一小时,耐涝又耐晒的父子俩不甘寂寞,去洗手间换了泳衣奔向泳池,享受嬉水的快活去了。而我缩在沙发上,众目睽睽、大庭广众之下,有一女郎假寐,在梦的工厂门口。
又来到凯恩斯机场,工作台前空荡而安静,只我们一行人前来办理乘机手续。顺利地过了安检,正在候机的客人也寥寥无几。就这样简简单单、云淡风清地告别了美丽迷人的凯恩斯,即将开始的第三次飞行,目的地将是悉尼。
机上的主要活动,还是与吃有关。机餐有羊肉饭和鸡肉饭两种选择,选了羊肉的。其实我本不饿,为了不枉羊肉饭来人间走一遭的光荣使命,不至于完全辱没它的曾经来过,象征性地尝了几口,汤汁里面加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紫菜,滑滑的,吃不出特别的味道。
继续攻读前几日未完成的功课,严歌岑的小说《小姨多鹤》。已近书的尾声,压抑了太久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,在我的老脸上,汹涌澎湃,老泪纵横,断了线的珍珠般,滚落个不停,默默地擦了又擦,如果此时身边空无一人,一定会放下手中的书,然后泣不成声。故事在那个嗜血的年代,一个名叫多鹤的日本女子,仿佛命中注定,无缘无故却又顺理成章地,将自己的命运与一群中国人紧密的连接在一起。那是血与肉的爱、魂与魄的疼,那是生活的赠予,生命的索取,那是夫妻之间、情人之间、朋友之间、亲人之间、甚至人与动物之间的真挚情感。生命应该得到尊重,多鹤并没有做错什么,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,不会因为她是侵入中国领土的日本人而心生鄙视,相反,她坚强的内心、执着的信念、绝境中求生的本领、多劫苦涩的命运,都深深地打动我。
把手表的指针拨快一小时,经过三个半小时的飞行,当地时间晚上20点10分,平安降落在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——悉尼。新南威尔士州位于澳大利亚版图的中间部分,介于维多利亚州与昆士兰州的中间。悉尼是澳大利亚最大、最古老的城市,也是澳大利亚最热闹的一个城市。为此,50%的华人移民后都选择在此居住,来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学生,也大多选择在悉尼就读。尽管如此,面积是深圳两倍的悉尼,人口却只有400万。悉尼作为城市的历史始于1788年,英国流放罪犯于此,是英国在澳大利亚最早建立的殖民地。二战后,大量欧洲、中东、东南亚的移民涌入澳大利亚,这些外来移民按人口数量来说,以意大利人居多,其次为黎巴嫩人、土耳其人、希腊人、华人和越南人。近20年来,华裔居民的数量如雨后春笋般激增,目前在悉尼地区的华裔人口大约在40万左右,占悉尼人口总数的10%。说到留学生,澳大利亚现有留学生40万,其中8万来自中国。不停地在想,在问,如果中国人不来澳大利亚……
取了行李,在机场稍等片刻,来自上海的吴导姗姗出镜。吴导的体型不算壮,腼着肚子迈着急切的碎步沉重出场,怀中抱着的纸箱里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,那是大家的晚餐,每人一个牛肉汉堡、一份薯条和一小瓶果汁。据说悉尼的夜晚,少有夜生活,尤其是可以大块朵颐的餐厅。
酒店和在墨尔本住过的同为一家,名为Citigate Sebel,位于28 Albion Street,Surry Hills。到达酒店,已经接近夜里十点钟了。垃圾晚餐的热气还没散尽,第一次尝试牛肉汉堡,肉质粗糙,酱料的口味也有些怪异。在国内城市里经常吃的洋式快餐,打进中国市场之前,应该是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研,在配方上做了中化处理的,因为原汁原味的东西,并不适合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因为习惯了中华美食,养尊处优而成的挑剔胃口。
真正的身处异国他乡,踩上云端的那一刻,已经将工作上的麻烦抛到九霄云外,也将身为大公司小职员的责任置之度外。打开被遗忘在行李里关了两天的手机,信息争先恐后地挤进来,有最不想听到的公司同事的电话,也有久无音讯的朋友的电话。怅然若失、恍若隔世。身处信息高速发达的电子化时代,人与人之间的距离,说远不远,说近不近。想它近时,它远在千里招之不来;而想它远时,它却近在咫尺挥之不去。人生之不如意,十之八九,因为谁都不是未卜先知的超人,谁都有懵懂无知的过去、身陷囹圄的困境、求之不得的心痛、欲罢不能的沉沦、欲壑难填的欲望、无力自拔又无能为力的尴尬。血肉之躯,是苦恼之源,为此尘缘难断。
